那天星期日樂得無事一身鬆,相約奪標倫到大球場看香港國際七人欖球邀請賽。
這兩個星期,兩份英文報章每天都連篇累牒地報導該項賽事的消息,一早便把這個活動炒熱,奇怪的是。中文報章竟然只得片言隻字,一熱一冷的對比,分別極大。
與奪標倫在茶樓吃了少許,於十二時來到球場,買了入場券(一百五十元一張),進入到球場,嚇了一跳,全場已經爆棚,場邊通通也站滿了人。舉目四望,到處都是鮮艷顏色的彩旗和裝飾,以及洋人觀眾的奇異打扮,令整個球場充滿嘉年華氣氛,而小孩子更歡樂非常,他們四處走動,開心不已,加上熱情奔放的洋姐洋婦與洋漢親熱的鏡頭隨處可見,更令人相信這個體育盛事是個歡樂的活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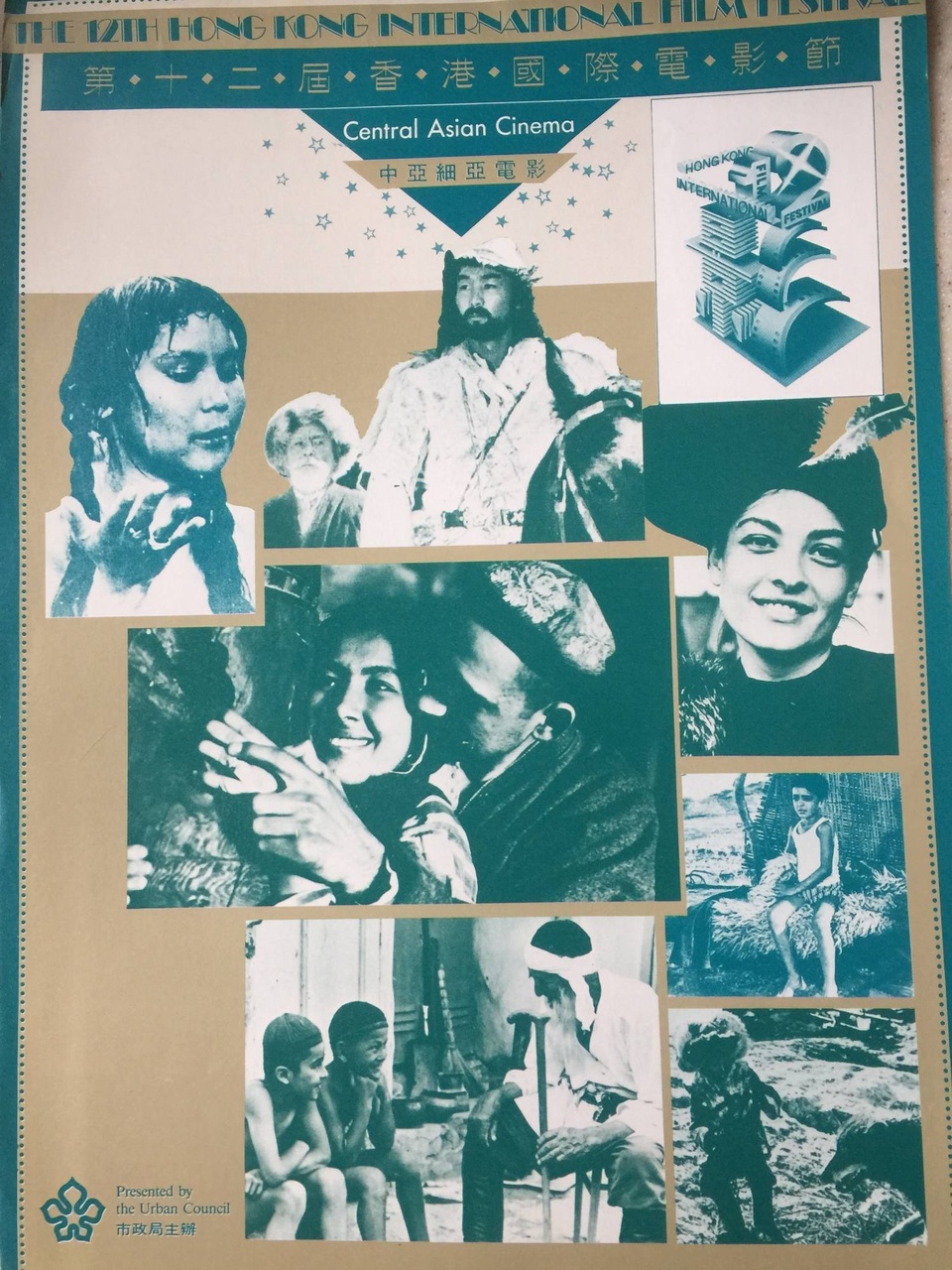
我與奪標倫繞場走了一週,觸目都是洋人,各個國家的人都有,相信全香港的外國人有一半都來到球場了。他們扮鬼扮馬,不斷為球隊打氣,情況熱烈,而又多彩多姿,一時間我與奪標倫都有身處異域的感覺。我曾經到過滿座的倫敦溫布萊球場,所見的情景跟我眼前的差不多完全一樣。
我與奪標倫各買了一罐啤酒,在近大鐘的看台找到了空位坐下來。旁邊一位洋漢與我聊天,他原來與朋友都是特別從外地飛來香港看球賽,他已經來看了二年,而明年他也預訂了酒店,會繼續來。他告訴我他是威爾殊人,他說威爾殊人打欖球,而英格蘭人踢足球。他自己卻從來不看足球。估不到今次在球場上竟然學曉了分辨威爾殊人與英格蘭人的方法。
七人欖球賽每場打二十分鐘,一場跟着一場,中間完全沒有休息,由於星期日的賽事全是淘汰賽,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認真的比賽,過程高潮迭起,緊張剌激兼而有之。七人賽得分比較容易,所以每場都有大比數,過癮的程度也就更大了。啤酒多飲了幾口之後,酒精開始上腦,情緒也愈來愈高漲,所以怪不得洋人球迷的行為開始放肆了。
正在看得興高采烈的時候。傳呼機響,原來是舊同學黃醫生急找,要我遠到他的家。為他的鐳射影碟店預備印製的片目校對錯字。這個訊息弄得我怒火中燒,奪標倫叫我不要回電,當沒有帶傳呼機在身。但我氣憤難平,星期日竟然要我開工,實在太過份了,於是我走到球場路邊,在臨時的公共電話亭回電話,說自己在享受生活,怎樣也不會在此時此刻工作,將來就算收不到酬勞也不計較了。在電話裡,只有我在說話,黃醫生說了些甚麼我全不理會。
回到看台上,已是銀碟的決賽,由台灣光華對杜拜放逐隊。光華隊在最後幾分鐘連下兩城,平反敗局,終於贏得冠軍,從港督手中取得銀碟,球員在繞場一週向觀眾致意時,現場二萬七千多外籍觀眾無不熱烈鼓掌,而在場的三、四百華人觀眾,更興奮異常。不過,其中也有例外,在我與奪標倫到場邊小食檔買熱狗填肚時,附近窗位老人家大聲講:「我今晚返屋企寫信俾新華社,問佢地點解唔派隊參加比賽,我地山東人咁大隻,廣東人又咁蠱惑,如果聯合組成一枝球隊,一定贏到冠軍,唔駛俾台灣佬威晒!我地十億中國人乜嘢人材都有,北京梗有一兩隊好勁嘅,只不過冇派落嚟之嘛!」
我與奪標倫面面相覷,他咬了一口熱狗,含含糊糊地說:「我諗住年尾移民加拿大,我諗我都係八月就走。」

散場時,我們順步走到銅鑼灣,沿途都見狂歡之後的洋人。他們的興奮情緒一直沒有冷靜下來,在街上你追我逐、大聲說笑和唱歌,路人為之側目。來到銅鑼灣地下鐵站,但見整個大堂全是似乎初次乘坐香港地下鐵的洋人,他們鑽來鑽去,喧嘩一片。我見到這個場面,便對奪標倫說:「不如過一陣先至坐車,帶你去我舊同學黃醫生嗰間鐳射影碟店睇一睇,嗰種生意而家有得做。」
自從去年股市崩潰之後,很多人的投資觀念都已經改變,從金融市場上退下來,轉而去搞小生意。舊同學黃醫生是個例子。我跟他很少見面,但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,說知道我熟電影、又做廣告,所以要我替他搞鐳射影碟店的宣傳單張和片目,但只要我做文字那一瓣,其餘設計和印刷由另一間公司負責。做這樣瑣碎而又沒有利錢的工作,我根本沒興趣,奈何他不時來電相求,我也當做幫朋友忙而勉強答應,連酬勞都沒講。
一接下工作方知泥足深陷,首先要時常到店子裡奔跑,構思好文字之後,又要在古怪的時間到他家開會,最無癮的是,自己寫的名字竟然被他踢到體無完膚。中國古語說:夏蟲不可語冰,我無謂跟他辯論,心只想着今次領一次教訓,以後不替熟人做這種友情幫忙的工作。
來到租賃店,熟識我的店員不在,我與奪標倫四處掌碟來看,店員猛向我們推銷他們的熱門勁碟。「許冠文、成龍、洪金寶啲戲我地都有喎!譚詠麟、梅艷芳、徐小鳳演唱會都嚟咗啦!嗰啲碟好搶手……唔知你地鍾意睇乜嘢碟呢?英文碟都有好多正★,鐵金剛每一集我地都有……。」
奪標倫問:「有冇NEW AGE MUSIC啲影碟?或者JAZZ嗰啲?」
「冇,我地冇咁舊嘅喋,我地入啲貨都係好新嘅。」
我與奪標倫又再次相對無言,似乎都同一時間發覺現時在香港,人與人溝通愈來愈困難,在步出影碟店的時候,我希望地下鐵的人潮已經散去。
#####
[ #1988 #張氏起居注 ]